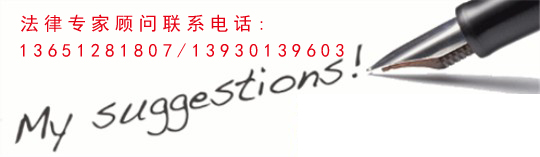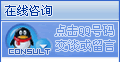公民概念在憲法文本中的發(fā)展
文章來源:中國憲政網(wǎng)
莫紀宏
“公民”概念①是指稱與具有完整主權特征的現(xiàn)代政治國家相對應的、作為主權國家構成要素之一的“居民”個人。在現(xiàn)代社會中,“公民”意味著個人屬于一個具有獨立完整主權、有一整套合法有序運作的國家權力運行機制的“政治國家”,“公民”是個人與主權國家之間的政治聯(lián)系的“價值屬性”,是人的自然特征與社會特征兩者的有機結合。依據(jù)法治原則,個人與主權國家之間的政治聯(lián)系是由“憲法”來加以規(guī)定的,因此,個人是否具有“公民”這種法律身份(從社會學上來講屬于“社會角色”),必須依賴于一個主權國家的憲法的明確界定。
我國自清末推行仿行憲政、將個人與國家之間的關系納入憲法的范圍以來,作為個人與國家之間的政治聯(lián)系的“公民”法律身份并不是從一開始就得到了憲法規(guī)范的明確肯定,其間經(jīng)歷了一個從“臣民”到“國民”,從“國民”到“人民”,從“人民”到“公民”的歷史發(fā)展過程。在個人獲得憲法上的“公民”法律身份的歷史發(fā)展過程中,個人與國家之間的政治聯(lián)系從從屬到平等、從不清晰到非常明確,“公民”概念使得個人與國家之間的政治聯(lián)系制度化、規(guī)范化和法律化,為“公民社會”、“法治國家”的建立奠定了憲法基礎。
一、新中國成立之前“公民”概念在憲法文本中的體現(xiàn)及特征
(一)從“臣民”到“國民”
新中國成立之前,在歷部憲法文本中,表述個人與國家之間政治聯(lián)系的概念并沒有出現(xiàn)“公民”一詞。1908年清政府通過的《欽定憲法大綱》采用了“臣民”一詞,但該大綱文本中也沒有出現(xiàn)與個人相對應的“國家”概念,只是使用了“大清帝國”。因此,在《欽定憲法大綱》中,個人與國家之間的政治聯(lián)系完全屬于“從屬性”的,個人是以“被統(tǒng)治者”的法律身份出現(xiàn)在憲法文本中的。
(二)“國民”與“人民”混用
辛亥革命勝利后,以孫中山先生為首的國民黨在南京成立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臨時政府為了光揚辛亥革命之勝利成果,以及限制日后上臺的袁世凱,于1912年3月11日頒布了《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該《臨時約法》在表述與“中華民國”相對應的個人的法律身份時,同時使用了“國民”和“人民”。但“國民”與“人民”作為憲法文本上所規(guī)定的個人的法律身份,兩者之間內涵究竟有什么差異,并不是很清晰。
1913年由當時所謂的“中華民國國會憲法起草委員會”擬定的《天壇憲法草案》,繼續(xù)沿用了“國民”與“人民”兩詞,但是,仍然沒有界定兩者之間的關系,以及是否指稱與國家相對應的個人。該憲法草案第三章“國民”,對“人民”的各項權利作出了詳細規(guī)定。并且在第3條明確地規(guī)定:“凡依法律所定屬中華民國國籍者,為中華民國人民”,首次提及“人民”資格的認定。很顯然,從立憲技術上來看,該憲法草案基本上是“國民”與“人民”概念混用。此后,1914年《中華民國約法》(又稱“袁記約法”)、1923年的《中華民國憲法》(史稱“賄選憲法”)皆依此做出規(guī)定。
1931年5月12日國民會議通過(同年6月1日國民政府公布)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以及1936年的《中華民國憲法草案》(史稱“五五憲草”)、1946年的《中華民國憲法》大同小異,皆以“國民”指稱國家主權的歸屬主體的每一分子或者具備中華民國國籍者,以“人民”概稱權利義務主體。但《訓政時期約法》又將“國民”與“人民”相結合,共同確認個人的各項憲法權利與義務。從上述各項規(guī)定來判斷,似乎可以推斷,在民國時期憲法文本上所規(guī)定的“國民”的整體范圍與“人民”的范圍大致上是一致的,“國民”表現(xiàn)的是個體,而“人民”表現(xiàn)的是集體。
(三)“公民”概念的法律表現(xiàn)
雖然“公民”概念沒有明確出現(xiàn)在各種憲法文本中,但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在一些重要的法律文件中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公民”概念,盡管所使用的“公民”概念與“國民”、“人民”概念的含義相混用,但作為與政治國家相對應的“公民”概念已經(jīng)引起了廣泛關注。
孫中山早在《中華革命黨總章》中規(guī)定了“革命時期”黨員的享受不同待遇的三種身份(等級身份),并把黨員和非黨員的區(qū)別限定為公民和非公民的區(qū)別:“(1)凡于革命軍未起義之前進黨者,名為首義黨員;首義黨員悉隸為元勛公民,得一切參政、執(zhí)政之優(yōu)先權。(2)凡于革命軍起義之后,革命政府成立以前進黨者,名為協(xié)助黨員;協(xié)助黨員得隸為有功公民,能得選舉及被選舉權利。(3)凡于革命政府成立之后進黨者,名曰普通黨員;普通黨員得隸為先進公民,享有選舉權利。”至于“非黨員,在革命時期內,不得有公民資格,必待憲法頒布之后,始得從憲法而獲得之”。②
與北洋政府、民國政府頒布的憲法文件不同的是,在中國共產(chǎn)黨建立的革命根據(jù)地制定和發(fā)布的憲法性文件,從一開始就肯定了“公民”概念。例如,1934年1月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修改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第4條規(guī)定:“在蘇維埃政權領域,工人、農民、紅色戰(zhàn)士及一切勞苦民眾和他們的家屬,不分男女、種族(漢、滿、蒙、回、藏、苗、黎和在中國的高麗、安南人)、宗教,在蘇維埃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皆為蘇維埃共和國的公民。為使工農兵勞苦民眾真正掌握自己的政權,蘇維埃選舉法特規(guī)定:“凡上屬蘇維埃公民,在十六歲以上者皆有蘇維埃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直接派代表參加各級工農兵蘇維埃的大會,討論和決定一切國家的、地方的政治任務。”
總之,從清末仿行憲政始到新中國成立止,近半個世紀的立憲活動,由于在憲法學理論上沒有對個人與國家之間的政治聯(lián)系在理論上和在制度上做出全面和有效的界定,因此,表述個人與國家之間政治聯(lián)系的法律術語自然也就呈現(xiàn)多元化的特點,從“臣民”到“國民”,從“國民”到“人民”、“公民”,這些概念在表述個人與國家之間的政治聯(lián)系方面都沒有完全制度化、規(guī)范化,存在著簡單借用和照搬國外憲法文本的問題,缺少具有中國特色的自成體系的解釋理論和制度規(guī)范。
二、新中國憲法發(fā)展過程中“公民”概念的沿革與特征
(一)《共同綱領》關于“人民”與“國民”的規(guī)定
在建國前夕誕生的起“臨時憲法”作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共同綱領》③中,還沒有產(chǎn)生與現(xiàn)代國家相對稱的“公民”的概念,只有作為社會革命運動的主力軍、具有濃厚政治色彩的“人民”的概念。國家還沒有從整體來承認每一個個體可以無條件地享有某些可以對抗國家的“基本權利”。這一點,從《共同綱領》第7條就可以充分反映出來。該條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必須鎮(zhèn)壓一切反革命活動,嚴厲懲罰一切勾結帝國主義、背叛祖國、反對人民民主事業(yè)的國民黨反革命戰(zhàn)爭罪犯和其他怙惡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對于一般的反動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資本家,在解除其武裝、削減其特殊勢力后,仍須依法在必要時期內剝奪他們的政治權利,但同時給予生活出路,并強迫他們在勞動中改造自己,成為新人。假如他們繼續(xù)進行反革命活動,必須予以嚴厲的制裁”。上述規(guī)定很顯然帶有革命和專政的色彩,并不存在由國家無條件予以保障的“公民的基本權利”。
《共同綱領》也使用了“國民”的概念,但對“國民”規(guī)定的是法律義務和道德義務。如《共同綱領》第8條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均有保衛(wèi)祖國、遵守法律、遵守勞動紀律、愛護公共財產(chǎn)、應征公役兵役和繳納賦稅的義務。”
從《共同綱領》關于“人民”和“國民”概念的相關規(guī)定來看,很顯然,作為權利主體的“人民”與作為義務主體的“國民”的法律性質以及所指稱的人群的范圍是不同的。作為權利主體的“人民”是一個整體概念,并不包括所有的人,只是人群中的“一部分”,而作為義務主體的“國民”則涉及到所有的個體。關于權利主體與義務主體的范圍不一致,周恩來在其所做的《關于〈共同綱領草案起草經(jīng)過和綱領的特點〉的報告》中作了辨析。“人民”是指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chǎn)階級、民族資產(chǎn)階級,以及從反動階級覺悟過來的某些愛國民主分子。“而對官僚資產(chǎn)階級在其財產(chǎn)被沒收和地主階級在其土地被分配以后,消極的是要嚴厲鎮(zhèn)壓他們的中間的反動活動,積極的是更多地要強迫他們勞動,使他們改造成為新人。在改變以前,他們不屬于人民范圍,但仍是中國的一個國民,暫時不給他們享受人民的權利,卻需要使他們遵守國民的義務。”④
值得注意的是,從《共同綱領》第7條的規(guī)定來看,不屬于“人民”的人應當指“勾結帝國主義、背叛祖國、反對人民民主事業(yè)的國民黨反革命戰(zhàn)爭罪犯和其他怙惡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一般的反動分子、封建地主、官僚資本家”,這些人沒有“政治權利”,但是“給予生活出路,并強迫他們在勞動中改造自己,成為新人”。這就意味著上述人員除了不享有作為“人民”中一成員依據(jù)《共同綱領》可以享有的政治權利之外,其他“權利”并沒有被剝奪,特別是作為自然人的基本生存權仍然得到了肯定。
總之,《共同綱領》由于在建國前夕誕生,因為并不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產(chǎn)生的,個人與國家的政治關系還受到了當時革命戰(zhàn)爭形勢的影響,所以,作為準確反映個人與國家政治聯(lián)系的“公民”概念自然也就無法生長,“人民”、“國民”作為過渡性的概念,在《共同綱領》中表述了作為與新民主主義國家相對應的個人的法律地位,這一現(xiàn)象既有歷史的局限性,也有歷史的必然性。
(二)“公民”概念正式進入憲法和法律文本
新中國最早使用“公民”概念的規(guī)范性文件是1953年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其第4條寫道:“凡年滿十八周歲之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不分民族、性別、職業(yè)、社會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財產(chǎn)狀況和居住期限,均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但通篇除此一處外,并沒有其他地方再次涉及到“公民”一詞。與此同時,為準備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做好選民登記工作而頒發(fā)的《全國人口調查登記辦法》的第3條規(guī)定:“凡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均應進行登記。”這樣的法律規(guī)定似乎表明了國民是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人,而公民資格是一個內涵更加豐富的詞匯,并不是取得國籍的當然結果。取得國家國籍即成為一個國家國民,但若沒有取得公民資格,就不一定是一個國家的公民。
“公民”概念正式出現(xiàn)在憲法文本中是1954年憲法。1954年憲法通過規(guī)定公民的基本權利,建立起以“公民”身份為基礎的人權制度,擴大了《共同綱領》所規(guī)定的憲法權利主體的范圍,奠定了新中國歷部憲法所確立的公民的基本權利的制度基礎,發(fā)展了人權的基本內涵。
以公民的基本權利為基礎,通過單獨設立一章“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建立我國公民的基本權利的完整法律結構。
1954年憲法雖然對人民的敵人的權利也作了必要的限制,但又通過規(guī)定“公民的基本權利”的方式來給予那些老老實實地改造的“封建地主、官僚資本家”以“生活出路”,也就是說,除了政治權利受到必要的限制之外,其他性質的“公民的基本權利”還是有條件地可以行使的。尤其是1954年憲法第85條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這一規(guī)定實際上是肯定了那些老老實實地改造的“封建地主、官僚資本家”在一般的憲法權利方面是與普通公民平等的。這就體現(xiàn)了現(xiàn)代憲法所強調的“國家與公民”相互對應的政治國家的基本法律特征。
1975年、1978年憲法雖然是在文革時期產(chǎn)生的,其中許多內容帶有極左思想的痕跡。但是,從制度構建的層面來看,1975年憲法對憲法權利的規(guī)定并沒有背離1954年憲法的宗旨,除了保留了1954年憲法所規(guī)定的“公民的基本權利”的權利體系和結構,而且,還根據(jù)當時的歷史條件,對“公民的基本權利”的內容做了適當?shù)卦鰷p,有些權利規(guī)定還帶有一定的歷史進步性,所以,從整體上來看,1975年憲法所確立的憲法權利制度在1954年憲法所確立的憲法權利制度上有所發(fā)展,而沒有出現(xiàn)明顯的倒退跡象。
從1954年、1975年和1978年憲法關于“公民”概念的規(guī)定來看,“公民”概念基本上是作為“基本權利”的權利主體而存在的。但由于受到建國以來各種政治因素的影響,對于“公民資格”在憲法文本中始終沒有加以確認,因此出現(xiàn)了有公民的基本權利的憲法規(guī)范,但卻沒有行使公民的基本權利的權利主體的界定。這種公民的基本權利制度的設計方式在法理上是存在嚴重缺陷的,在制度實踐中也不利于真正建立起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實現(xiàn)的具體法律保障制度。
(三)1982年憲法確定了“公民資格”,豐富和完善了公民的基本權利制度
1982年憲法關于憲法權利和公民的基本權利的一系列規(guī)定構成了我國現(xiàn)行的完整的憲法權利和公民的基本權利體系和結構,是建國以來最好的一部憲法。一方面,在保護公民的基本權利和保障憲法權利方面,1982年憲法比較全面地恢復了1954年憲法的良好傳統(tǒng),肯定了1954年憲法中許多有益的、符合人權保障事業(yè)進步發(fā)展要求的規(guī)定;另一方面,1982年憲法又根據(jù)我國的具體國情,豐富和完善了憲法權利和公民的基本權利,增設了許多新的權利,體現(xiàn)了該憲法在保障憲法權利和保護公民的基本權利方面所具有的先進理念。
1982年憲法比較全面地規(guī)定了公民的基本權利,建立起完善的公民的基本權利體系和結構,特別是在憲法中突出了公民的基本權利在整個憲法中的地位,一改1954年憲法、1975年憲法和1978年憲法的傳統(tǒng),將“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作為第二章,放在第三章“國家機構”的前面,表明了公民的基本權利與國家機關之間的權力之間的目的和手段的關系,理順了國家權力與公民權利的關系,符合現(xiàn)代憲法的基本精神。1982年憲法在第二章用整章內容確立了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如選舉權和被選舉權,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和示威自由的權利,宗教信仰自由權,受教育權等等。
1982年憲法除了規(guī)定了公民的基本權利之外,對于憲法權利的保障還涉及到了其他權利主體,這些權利主體依據(jù)憲法享有以下憲法權利:
(1)勞動者的權利
1982年憲法第43條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勞動者有休息的權利”;“國家發(fā)展勞動者休息和修養(yǎng)的設施,規(guī)定職工的工作時間和休假制度”。第8條也規(guī)定:“參加農村集體經(jīng)濟組織的勞動者,有權在法律規(guī)定的范圍內經(jīng)營自留地、自留山、家庭副業(yè)和飼養(yǎng)自留畜。”
(2)企業(yè)事業(yè)組織的職工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權利
1982年憲法第44條規(guī)定:“國家依照法律規(guī)定實行企業(yè)事業(yè)組織的職工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退休制度。退休人員的生活受到國家和社會的保障。”
(3)婦女的權利
1982年憲法第48條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婦女在政治的、經(jīng)濟的、文化的、社會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權利”;“國家保護婦女的權利和利益,實行男女同工同酬,培養(yǎng)和選拔婦女干部”。
(4)婚姻、家庭、母親和兒童受國家的保護
1982年憲法第49條第1款規(guī)定:“婚姻、家庭、母親和兒童受國家的保護。”
(5)華僑的權利
1982年憲法第50條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保護華僑的正當?shù)臋嗬屠妗!?/DIV>
(6)歸僑和僑眷的權利
1982年憲法第50條規(guī)定:“保護歸僑和僑眷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
(7)殘廢軍人、烈士軍屬和軍人家屬的權利
1982年憲法第45條第2款規(guī)定:“國家和社會保障殘廢軍人的生活,撫恤烈士家屬,優(yōu)待軍人家屬。”
(8)盲、聾、啞和其他有殘疾的公民的權利
1982年憲法第45條第3款規(guī)定:“國家和社會幫助安排盲、聾、啞和其他有殘疾的公民的勞動、生活和教育。”
(9)外國人的權利
1982年憲法涉及到外國人的權利有幾處規(guī)定,主要有第32條的規(guī)定,即“中華人民共和國保護在中國境內的外國人的合法權利和利益,在中國境內的外國人必須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中華人民共和國對于因為政治原因要求避難的外國人,可以給予受庇護的權利”。第18條也規(guī)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允許外國個人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的規(guī)定在中國投資,同中國的企業(yè)或者其他經(jīng)濟組織進行各種形式的經(jīng)濟合作。
(10)選民的權利
1982年憲法第102條第1款規(guī)定:“縣、不設區(qū)的市、市轄區(qū)、鄉(xiāng)、民族鄉(xiāng)、鎮(zhèn)的人民代表大會受選民的監(jiān)督”;“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選舉單位和選民有權依照法律規(guī)定的程序罷免由他們選出的代表。”
(11)被告人的權利
1982年憲法第125條規(guī)定:“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
從1982年憲法關于“公民”的法律地位的各項規(guī)定來看,個人與國家之間的政治聯(lián)系,通過公民資格的確認、公民的基本權利的保護得到了全面的規(guī)范。至此,通過憲法文本的規(guī)定,個人與國家之間的政治聯(lián)系完全制度化、法律化。除了以公民的基本權利來確立公民個人與國家、國家機關之間的一般性法律聯(lián)系之外,還通過規(guī)定勞動者、被告人等特定主體的憲法權利,進一步豐富和發(fā)展了個人與國家之間政治聯(lián)系的內涵。從人權保障的立場出發(fā),由于“普遍人權”概念在2004年被確立在憲法文本中,因此,個人逐漸從法律身份到自然人身份來與政治國家發(fā)生政治關系,政治國家對作為主權國家構成要素之一的居民的“道德義務”日趨增強,個人與國家之間關系的領域日益擴展。
(四)“公民”概念作為確認個人與國家之間政治聯(lián)系的制度術語具有歷史的局限性
1982年憲法產(chǎn)生以后,我國的人權保障事業(yè)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fā)展。特別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以后,隨著我國在國際人權領域所開展的人權斗爭的不斷勝利,在反駁少數(shù)敵視我國人權政策的國家的挑釁言論的同時,我們也對國際社會的人權保障的最新趨勢和動向有了全新的了解,在人權的基本觀念上也糾正了原先一些不太準確和不太科學的看法和認識。特別是在1997年和1998年我國政府先后簽署了《經(jīng)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肯定了國際人權公約中的普遍人權的基本觀念。2001年2月1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批準了《經(jīng)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根據(jù)該公約的要求,我國政府將于2005年3月份聯(lián)合國人權會議期間向人權委員會提交中國實施《經(jīng)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的具體情況。針對我國人權保障事業(yè)不斷與國際社會接軌的情況,2004年3月14日由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將“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進了憲法。這里的“人權”應當理解成國際人權公約所規(guī)定的普遍人權意義上的人權,也就是說適用于締約國境內所有自然人的權利。因此,如果不將此次憲法修改所加入的“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中的“人權”理解成國際人權公約意義上的普遍人權,這樣的規(guī)定實際上是沒有任何意義的。因為從1954年憲法到1982年現(xiàn)行憲法,保障人權一直是我國憲法在設計憲法權利制度時的首要指導原則,只不過我國憲法中所規(guī)定的憲法權利,包括公民的基本權利在內,享有憲法權利的權利主體的普遍性還沒有擴展到所有的自然人。公民的基本權利也只適用于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公民,而外國人的權利在憲法上是通過特殊的憲法權利制度來加以保護的。根據(jù)我國歷部憲法關于憲法權利的規(guī)定,還不存在適用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所有自然人的一類憲法權利。如果此次修憲寫進憲法的“人權”的含義不是國際人權公約中的普遍人權意義上的人權,那么,這樣的人權概念寫進憲法是沒有多少意義的,相反還會對我國建國以來國家在保障人權事業(yè)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就產(chǎn)生負面的影響。其實,即便在文革時期出臺的1975年憲法,不僅規(guī)定了比較詳細的公民的基本權利和其他性質的憲法權利,而且也強調了保護公民權利是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基本職責。所以,“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如果是傳統(tǒng)人權意義上的,那么這種規(guī)定是多此一舉的。所以,2004年修憲引進的“人權”概念應當是普遍人權意義上。人權概念入憲,改變了我國傳統(tǒng)憲法中所規(guī)定的人權保障模式和憲法權利的結構,將政府在保障人權方面的責任擴展到包括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生活和工作的所有自然人都享有的某些基本人權,這些基本人權比起公民的基本權利來說,更具有基礎性的保障作用。不過,這樣的普遍人權與傳統(tǒng)的憲法所規(guī)定的公民的基本權利的內涵并不矛盾,而是相互補充的關系。將普遍人權的概念引入憲法,一方面肯定了傳統(tǒng)憲法對各項公民的基本權利的保護,另一方面,傳統(tǒng)憲法所規(guī)定的公民的基本權利在人權保障事業(yè)中仍然具有獨立的價值,具有不同于普遍人權的獨立的人權保護領域。對于不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外國人、無國籍人以及其他性質的自然人來說,除了可以享受國際人權公約所規(guī)定的人權保護標準之外,并不能在法律上當然與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公民享有同等數(shù)量和范圍的憲法權利。作為公民權利,其權利內涵和范圍要比普遍人權意義上的人權要更加廣泛和深入。
因此,2004年修憲將人權的概念寫進憲法,豐富了我國現(xiàn)行憲法關于憲法權利和公民的基本權利制度的內容,擴大了憲法權利主體的范圍和憲法權利的深度和廣度,使得人權保障事業(yè)獲得了更加可靠的憲法保障。“人權”概念入憲擴大了國家對個人應當承擔的道德義務的范圍,突破了“公民”概念對個人與國家之間政治關系法律界定的界限,豐富了現(xiàn)代憲政原則的內涵,為作為根本法的憲法更好地發(fā)揮維護政治國家的“國家主權”、規(guī)范國家機關的權力行使秩序、保護個人合法和正當?shù)姆蓹嘁娴确矫娴淖饔茫峁┝擞行У闹贫缺U稀?/DIV>
參考文獻:
①“公民”一詞是舶來品。它最初進入中國人的政治語匯的時間應該是在20世紀初,大致是出現(xiàn)在近代文人志士介紹西方憲法的著作中,如康有為就曾發(fā)表《公民自治篇》。康有為是較早提出近代意義的“公民”概念的人,也是最早主張“立公民”的人。參見王振東:《人權:從世界到中國》,黨建讀物出版社1999年版。
②參見《中華革命黨總章》,載《孫中山全集》第三卷,中華書局1984年版。
③1949年9月29日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
④《人民日報》1949年9月26日,轉引自許崇德主編:《中國憲法參考資料選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
作者簡介:莫紀宏(1965—),男,江蘇省靖江市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人權研究會理事、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研究方向:憲法、行政法。
載《人權雜志》2010年第3期
(聲明:本站所使用圖片及文章如無注明本站原創(chuàng)均為網(wǎng)上轉載而來,本站刊載內容以共享和研究為目的,如對刊載內容有異議,請聯(lián)系本站站長。本站文章標有原創(chuàng)文章字樣或者署名本站律師姓名者,轉載時請務必注明出處和作者,否則將追究其法律責任。) |